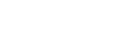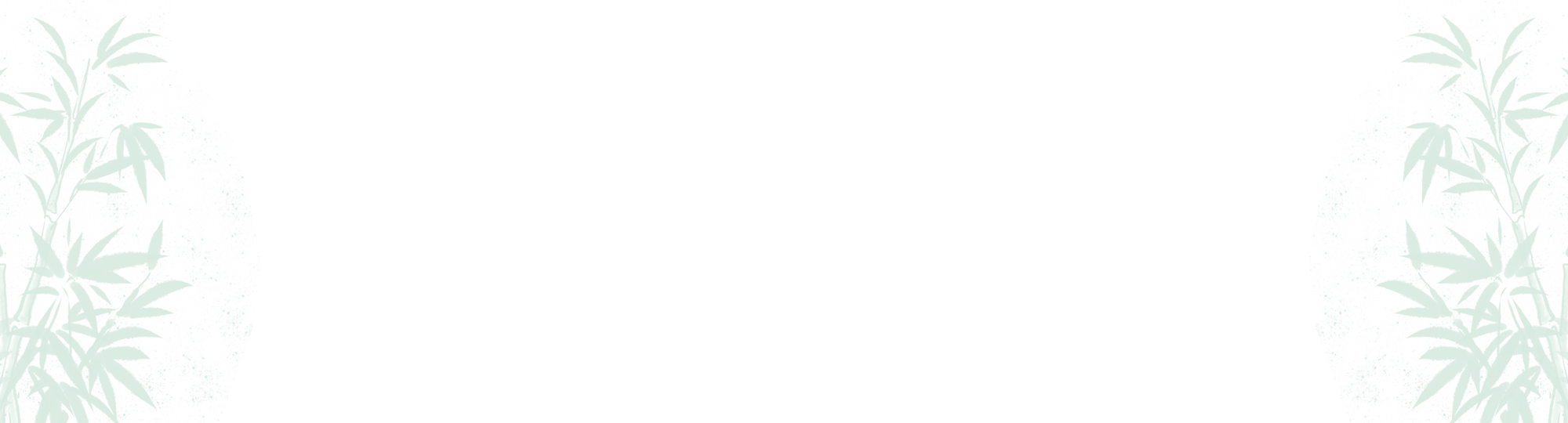泱泱華夏,源遠流長,數千年的歷史演變讓中華民族積累了很多優秀的文化和技藝。
在眾多傳統文化技藝當中,有一門文化技藝雖然極具觀賞性,但是比較冷門,不為大眾所熟知,這就是“竹海飛人”。
“竹海飛人”,顧名思義就是在竹林里穿梭,猶如飛行一般。
“竹海飛人”其實并不是一項為了表演而衍生出來的技藝,而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一門手藝。

竹上行走,身輕似燕
浙江省寧波市奉化石門村有竹林萬畝,漫山遍野的青翠將石門村裝扮得格外壯觀。
滿山竹林成就了奉化石門村,石門村的村民生存自然也就離不開竹子。
竹子的生長速度很快,不用多長時間就能夠長得很高。
雖然長得高,但竹子受不了打擊,每當風雨之后,竹林里都是一片狼藉,令竹農們損失慘重。
為了讓竹子更好地生長、減少經濟損失,竹農們會在臺風、暴雪等惡劣氣候來臨之前,爬上竹梢,將最頂端的一節竹子砍下。

這樣一來,竹子的高度降低,經風能力就提高了,竹葉的壓力也減小了,能夠有效地減少竹林因為惡劣天氣帶來的經濟損失。
砍掉最頂端的竹腦,聽上去好像很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卻讓人看得提心吊膽。
人要爬上好幾米高、但是支撐能力并不是很堅固的竹子,竹子還會時不時受到風向影響而擺動。
攀爬本來就已經是一件難事,還要附著在竹子上砍下竹腦,更是難上加難。

即使困難,為了減少經濟損失,竹農們也不得不這么做,久而久之,竹農們就掌握了技巧,越發熟練起來。
為了節省更多的時間,有的竹農會在砍完一根毛竹之后,利用這根毛竹本身的彈性,從這根毛竹上彈跳到另一根相近的毛竹上。
這樣的畫面,看上去好像武俠小說當中的絕世高手:竹農們在竹林之間穿梭,竹葉沙沙作響,人在竹子間來回跳躍,腳步輕盈,落腳準確,動作利落,身姿優美。
竹農們在竹林之間穿梭的樣子讓觀看者目不暇接,無一不拍手叫好,嘖嘖稱贊。

“飛行”在竹林之間的竹農們,也逐漸有了“竹海飛人”的稱號。
竹上行走本領的背后,是無數次練習換來的“藝高人膽大”與“熟能生巧”,這要求“竹海飛人”們在竹林間行走時,精神要高度集中,眼、手、腦、腳都要相互配合,這依靠的不僅僅是熟練的技術,更重要的還有過人的膽識。
利用竹子的彈性飛躍到另一根柱子上,如果下腳不準,很有可能被竹子彈出去,摔倒在地,所以每一次移動都是膽識與細心的考驗。
高速的移動一旦碰到什么,都會造成劃傷,更何況,每位“竹海飛人”身上都帶著磨得十分鋒利的刀具。

有危險、有難度,才讓這項技藝顯得尤其珍貴,但也正是因為危險性太高,讓“竹海飛人”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從前會的人大多年齡漸長,不再適合做這樣的高難度動作;而年輕人也不愿意來學,因為危險望而卻步。
于是,這項曾經收獲無數掌聲和叫好的技藝逐漸無人問津起來。
現在還能夠表演“竹海飛人”的人可謂是少之又少,石門村現在還掌握“竹海飛人“技藝的也只有毛木信、毛裕自、毛邵興三位老人了。
這三位老人年紀都已超過五十歲,最小的毛紹興今年53歲,最大的毛木信今年剛滿60歲。

年過半百,仍在竹子上行走
“竹海飛人”一般都是從小練起,他們大多數都是還不滿十歲就接觸,十幾歲就已經能夠在竹子上爬上爬下了。
竹林里的竹子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每一根都不一樣。
不同的竹子的顏色,粗細,根部都不一樣,有的竹子看上去又高又壯,但是很有可能是新竹,支撐能力不強,無法承受人在竹子上的活動。
有的竹子上帶有瘢痕,這很可能就是被蟲蛀過的竹子,不夠結實,而對竹子的判別,完全依靠“竹海飛人”自己的經驗。

毛木信說:“干這個活兒一定要膽大心細,除了從小鍛煉出來的手腳功夫外,眼力也很重要,要學會從竹的顏色、粗細、根部,對一棵竹的年齡和承受能力做出一個迅速而正確的判斷,2年以下的新竹,竹梢較小,承受能力較差,一般不用理它。另外帶有傷疤的竹子,極可能遭到了蟲蛀,也不能用來支撐體重。”
根據毛木信自己的介紹,他從小就在竹林里玩,對于竹林里的竹子可以說是了如指掌。
長大之后,毛木信就開始了“削竹腦”的工作。

毛木信的動作很快,一天下來能削好幾畝竹林,少說也有一千多根竹子。
毛木信的一天從太陽上山開始,早飯過后就要去竹林,一直到晌午時分才出來吃午飯。
吃過午飯之后,毛木信稍作休息,又要開始重復上午的工作,有時候忙起來,毛木信要在竹子上從早待到晚。
毛木信把十來棵“大毛筒”的竹梢綁到一起,做成巨型鳥窩的樣子,這樣,人就能夠在竹子上穩穩地坐住,中午時還可以坐著吃完午飯。

“削竹腦”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毛木信卻比較樂觀。
他尤其喜歡夏天的時候做工,竹林里比外面涼爽,自己坐在竹梢上,舒坦自在。
現在的毛木信已經邁入花甲之年,但依然堅持在做“竹海飛人”的事情。
因為“竹海飛人”陪伴了毛木信一輩子,已經成為毛木信生命力難以割舍的一部分,對于自己的這項手藝,毛木信是自豪與驕傲的。

無人傳承,境地尷尬
關于“竹海飛人”的來源已經無法考證,根據奉化石門村村民的描述,這項技藝少說也有百年的歷史。
如果非要追溯的話,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蹤跡。
2008年的時候,寧波市將“竹海飛人”技藝列入寧波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雖然現在“竹海飛人”不再景氣,但它曾經也風靡一時、成為奉化地區的驕傲。
因為極具觀賞性和高難度,“竹海飛人”不止一次出現在鏡頭中,從奉化石門村走向全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拍攝了科教片《石門毛竹》,專門介紹奉化石門村的毛竹,其中就有“竹海飛人”的鏡頭。
鏡頭中,藝人借助竹子彈力在竹子之間穿梭的樣子讓無數觀看過紀錄片的觀眾都嘆為觀止,“竹海飛人”也因此被譽為“中華一絕”。
2005年,寧波市在整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注意到“竹海飛人”,寧波市電視臺特意在溪口鎮石門村的青山盤頭,拍攝了這一絕活。

隨著“竹海飛人”的名聲越來越大,央視十臺經典節目《走進科學》也慕名前往石門村,只為一探“竹海飛人”的風姿。
節目一經播出,不僅“竹海飛人”火遍全國,石門村也被世人所矚目。
2006年,日本關西電視臺專門趕赴石門村,只為一睹“竹海飛人”的風采。
在拍攝的過程中,日本關西電視臺上海支局長中嶼順也,被毛紹興、毛木信和毛裕自三位老人的表演徹底折服。

中嶼順也說:“我們最早是從湖南衛視看到浙江奉化有表演這種絕技的奇人,能像《臥虎藏龍》里的周潤發,章子怡一樣在竹梢上飛來飛去,還不用威亞和保險帶,當時就覺得很震驚….三位竹海飛人的絕技,讓我們大開眼見,石門村風景美麗,有竹林有小溪,跟詩詞里的中國鄉村一個意境。我們工作生活在大都市里,看慣了高樓大廈,來到這里感到非常的親切……相信隨著節目在日本的播出,會有更多日本人對奉化石門村,‘竹海飛人’產生濃厚興趣。”
可見,“竹海飛人”不僅走出了石門村,還走出了中國,傳播到了海外。
但是“竹海飛人”的難度和危險都是可見的高,這就導致愿意學習“竹海飛人”的人越來越少。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農村的年輕人都選擇外出務工,很少愿意留在村子里,更不要說學習“竹海飛人”這項技藝來養家糊口了。
因為擔心后繼無人的局面,石門村的“竹海飛人”們也曾經走出石門村,向外面傳授技藝。
但是,“竹海飛人”最看重的還是從小積累起的經驗,并不是掌握技巧就能在一朝一夕之間練成的事情。
出門授課的“竹海飛人”之一——毛康達說:“近處去過象山,稍遠的地方也到過安吉,短暫的培訓也只能教授一些皮毛。”

目前來說,“竹海飛人”的處境比較尷尬。
經過媒體的報道和宣傳,“竹海飛人”走出奉化地區,被全國人民所知。
很多人在看過“竹海飛人”后心生向往,前往石門村學藝,但是大多數都沒有童子功,是學不成“竹海飛人”的。
“竹海飛人”因只在奉化一帶流傳,與其他傳統技藝不同的是,它沒有門派之分,更沒有什么傳承體系,這樣一來,要想把“竹海飛人”傳下去就更難了。

面臨轉型,可惜獨門絕技將失傳
“竹海飛人” 其實就是因為“削竹腦”而發展出來的一門技藝,如今,隨著石門村毛竹生產比重的相應減少,“削竹腦”這項生產技藝面臨著衰落,“竹海飛人”也漸漸的演化為一種表演形式。
毛方定是“竹海飛人”新的傳承人,他從8歲開始爬竹子,16歲開始削竹腦,這項工作,毛方定已經干了幾十年了。
隨著村子里的竹子產業漸漸規模化、機械化,毛方定的日常工作已經從在竹林中穿梭,變成了在村子邊的工廠里用機器為竹子削皮。
“竹海飛人”對于毛方定來說,已經成了記憶里的東西,盡管現在,五十多歲的他還能夠利落地在竹林里爬上爬下,但是因為危險性太高,家里人已經不允許他再這樣做。

隨著“竹海飛人”們的逐漸老去,石門村的竹林之間也很難再見到竹葉婆娑、人飛竹搖的景象了。
這項技藝最終會走向何處無人知曉,但是沒人會希望,這項猶如武俠小說中絕世輕功一樣的技藝消失。
傳統與現實發生沖突,誰去誰留成了難題。

首頁

會員中心

電話